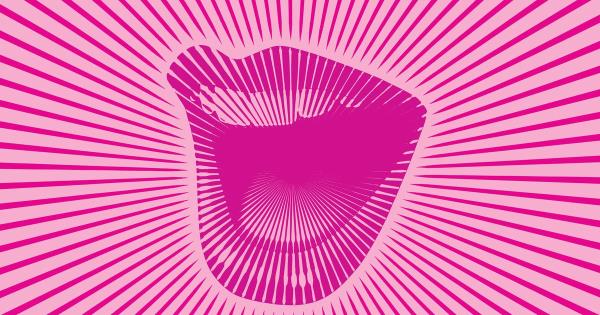夏威夷,拉海纳——瓦尔·卡斯科和她的家人在他们被焚毁的家的废墟中搜寻。
她的一个儿子凯西(Casey)在寻找姨妈的骨灰盒。另一个儿子埃里克(Eric)捡起了瓦尔的珠宝——发现了一个只有烟灰的小盒子,他母亲的结婚戒指蒸发了。孙子们喊着瓦尔的猫,没有回应。
两周零两天前,一场地狱般的大火席卷了拉海纳(Lahaina),这座夏威夷小镇变得面目全非,居民们在灾难中挣扎。
数百个像卡斯科斯这样的家庭流离失所,试图在美国100多年来最致命的野火之后为他们的生活制定新的轨道。房屋、汽车和珍贵的物品被大火吞噬,随之而来的是任何安全感、稳定感或安全感。
瓦尔和她的家人第一次回来,看看他们的家还剩下什么——这个家曾经是她妈妈的,在那之前是她祖母的。
没有太多。
只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地基,堆在一起的煤渣砖让人想起了马洛街(Malo Street)上一栋四居室的单层住宅,从那里可以俯瞰波光粼粼的太平洋。
在曾经的厨房里,一个弯曲的冰箱,一个扭曲的水槽顶部和一个烧焦的烤箱挤在一起。炉子上放着一只发黑的锅。
卡斯科一家试图通过记忆来追溯他们的足迹,回忆卧室曾经的位置和浴室的位置。空气中弥漫着烧焦、酸味和塑料味。
30分钟后,瓦尔和她的家人开车离开了。她的眼里闪着泪光,但没有一滴落下。
这位67岁的老人说:“就好像我根本没在看我的家。”“我甚至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但那不是我的家。”
那天早些时候,瓦尔被告知,她在当地一家酒店的临时住所将在大约两周内用完。自火灾以来,她和她的家人似乎已经无数次失去了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你以为你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准备退休了,”瓦尔说。“然后突然之间,你就不是了。你要重新开始。你一无所有。”
火灾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拉海纳的家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是否会重建,如何重建,何时重建——他们经常不确定最基本的事情,比如他们将在哪里睡觉。许多人从一个住处跳到另一个住处,想找个地方住下来。一些人在西毛伊岛与亲人一起避难,带着十几个或更多的人回家。在这个依赖旅游业的岛上,其他人在他们工作的酒店里找到了临时避难所,而更多的人则依靠毛伊县、红十字会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建立的官方资源。
最初推动幸存者前进的近乎狂躁的肾上腺素已经开始消散。现在,更糟糕的事情来了:在漫长而复杂的复苏之旅中,他们面临着沉重的负担。
那些在红十字会寻求住房援助的人排了四个小时的队。红十字会告诉卡斯科斯,他们在预订酒店房间的名单上大约排在第130位。待在地狱边缘是一种痛苦。
“我已经排了很多队了,”瓦尔说,回到他们很快就要搬出的酒店房间。“这就是现在的生活,排队等候。我知道你必须要有耐心,但我已经厌倦了耐心。”
“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她68岁的丈夫卡利(Kali)叹息道。
他们的大儿子瑞安(Ryan)住在瓦胡岛(Oahu),他疯狂地为父母找房子。红十字会将提供另一个临时选择;瓦尔说,他坚持认为他们需要更持久的东西。她同意了。“当你不得不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时……我觉得我又一次流离失所了。”
38岁的卡莉和凯西也搜遍了房源。在毛伊岛,选择余地很小,在火灾发生之前,毛伊岛的市场就已经紧张了。挂牌出租的公寓和房屋要么太小,要么太贵,要么需要爬楼梯,这是卡莉和瓦尔必须避免的。
“哦,一套三室两卫的房子,”卡利在酒店的沙发上兴奋地宣布,透过手机向外张望。“哦,是3600美元。”
Ryan, 45岁,facetime。“我想我找到了一套两室两卫的房子。这在我们的预算范围内,”他告诉瓦尔。
但她说,Val和Kali各有一间卧室,Casey各有一间,他们的孙子孙女就没地方住了。
“我在喜平也试过另一种。猜猜他们要收多少钱?6000美元!”瑞恩说。
8月8日,正是大风提醒瓦尔有些事情不对劲。她说,一整天都没有电,风以一种她从未听过的方式咆哮着。她、卡莉和凯西呆在家里,以为风暴会过去。
瓦尔的二儿子埃里克(Eric)和妻子雷(Lei)打电话说,他们公寓的屋顶被吹掉了。他们和三个年幼的儿子住在离这里大约一英里的地方。这家五口人逃离了拉海纳的中心地带,为了安全与其他家人一起住在马洛街。
但没持续多久。风也刮掉了屋顶,把一家人都刮得狼狈不堪。他们在车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这家人出现在了卡莉哥哥在纳比利的家门口。“拉海娜走了,”瓦尔说,泪流满面。
埃里克和雷的公寓被夷为平地;他们的孩子应该就读的小学被夷为平地。瓦尔的表姐的家也是如此,她家在马洛街(Malo Street)上与她的家相邻;另一个表亲的家,就在他们后面,在同一块土地上,也消失了。瓦尔和卡莉的也一样。
瓦尔说,灾难发生后的日子一片模糊。多达20人睡在Napili森林绿色的房子里。亲人们从房间里涌出来,躺在沙发上,在地板上占有一席之地。由于没有手机信号或电力,几乎没有关于发生了什么或即将发生什么的消息。
但没过几天,家里就收到了很多捐款。麦片、格兰诺拉麦片和午餐肉多得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笑着说:“我有一年的厕纸,但没有地方住。”
有了多余的食物可以分享,卡斯科一家开始每天晚上在前院举行晚宴。邻居、朋友和任何路过的人都被邀请到盘子里。
一天晚上,在拉海纳金色的晚霞下,晚餐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家人的闲聊中响起了一首名为《拉海娜长大了》(Lahaina Grown)的歌曲。孩子们四处乱窜。一棵鸡蛋花树在院子的入口处欢迎游客,它细长的树枝在车道上投下阴影。
它无法掩盖恐惧。烧烤架上的排骨嘶嘶作响,42岁的埃里克讲述了他在火灾发生后第二天偷偷溜回镇上所看到的情景——一个家庭在原地被烧成石化,跪着祈祷。“闻起来像肉的味道。”他摇着头说。
大人们挤在车道周围的口袋里。谈话,有时开玩笑,小心翼翼地围绕着悲剧。
“一个尺码不适合所有人,”瓦尔对聚集在一起的妇女们开玩笑说,她收到了成堆的捐赠衣服。“我也不会穿印花紧身衣。就因为我失去了一切,并不意味着我要穿别人给我的衣服。”
她责怪自己把她最喜欢的黑裤子落下了。她希望自己有指甲油,她需要办一张新的借记卡。每天,她都会想起她失去的另一件小东西。
夜幕降临,一家人开始规划未来的日子。埃里克、雷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准备在那个周末搬进纳比利的一套公寓,这是一位岛外亲戚提供给他们的。瓦尔、卡利和凯西计划搬进酒店,通过他们与酒店管理层的关系进行协调;瓦尔和卡莉经营着一家园林绿化公司,在那里提供服务。
即使是暂时的住所,他们也很感激。
瓦尔在马洛街的家里长大。她曾就读于那所被毁的小学,她记得和同学们一起爬上附近的古榕树,等着放学后的父母。她的未来被拉海纳鲁纳高中(Lahainaluna High School)所设定,这是该镇受人尊敬的地标。
瓦尔笑着说,卡利比她年长一年,“而且是一个受欢迎的运动员。”“我只是一个简单、普通的女孩。”他们成为了朋友,直到他去加州上大学。“他会给我写信,结尾总是说‘爱你的,永远’,我妈妈会说,‘嘿,这个男孩喜欢你。’”她毕业去瓦胡岛上大学后,这些情书还在继续。她保留了每一个。那些也在大火中消失了。
在临时旅馆里,桌上摆着一瓶栀子花。那天早上,卡莉为瓦尔挑选了这些衣服——这是这个稀稀拉拉的套间里为数不多的个人风格之一。
“这是一家酒店,不是家,”瓦尔强调说。但这座建筑足够坚固,可以保护她免受风的伤害,现在风一上来就会引发焦虑。
她整个上午都在打电话,试图切断家里的公用设施。她说,垃圾处理机构告诉她,他们需要收到一封信,才能停止向她的地址提供服务。“我的身体开始发热。我的房子被烧毁了。我甚至没有纸。我该怎么寄信呢?”
每一项任务都很艰巨。自从火灾发生前,瓦尔就一直戴着同一套眼神交流眼镜——现在因为泪水而变得模糊了——但是领取替换眼镜的队伍太长了。卡利在7月的心脏手术后的医疗预约都被推迟了,需要重新安排。
她经常坐在阳台上,凝视着大海,审视着下面原始的庭院——一个远离拉海纳废墟的世界。
卡斯科一家又在纳比利的院子里聚在一起吃晚饭。这一次,没有任何音乐播放。这群人也比较稀疏,因为一些家庭成员不在那里——他们是在火灾发生后飞过来帮忙的亲人。
埃里克和瓦尔讨论了在当地一家披萨店附近发现另一具尸体的消息。“我听说他们发现他被烧死在他的卡车里,”埃里克说。“我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
“也许他是想出去,”瓦尔叹了口气。
凯西提前结束了。“我想回家睡觉,”他说着,向大家挥手告别。“嗯,酒店。不在家。”
第二天晚上是Eric和Lei的一个儿子的11岁生日。他们通常会在海滩上度过一天,但今年在纳比利家的院子里吃晚饭就足够了,父母说。
当寿星华立凯手里拿着两块蛋糕,神情严肃地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院子时,太阳已经下山,风也开始起了。雷跟在后面,端着盛着食物的铝托盘。她看上去很疲惫——眼睛疲倦,嘴唇紧闭。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34岁的雷坐在她的堂兄肯尼迪旁边的露营椅上。
“你看起来像是哭了一整天,”肯尼迪低声说。
“这只是睡眠不足。一切都在赶上来。我的身体好像在停止运转,”雷说。“该吃的时候我不吃。我睡不着。”新公寓还是没有家的感觉。
她9岁的儿子哈威亚(Hawea)在派对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独自坐着,他说他想睡觉了。他躺在家里的一辆车里,但几分钟后他就跑了回来,抓住了他的奶奶。那天晚上风很大,把汽车刮得格格作响。“风,现在把他们吓坏了,”瓦尔低声说,“自从火灾那晚他们的屋顶被刮掉了。”
埃里克和雷在纳比利的新公寓是一间舒适的两居室,家具和电器都是用捐赠拼凑起来的。在勘察完马洛街(Malo Street)家的废墟后,瓦尔和卡利第一次顺道来看了看。
角落里挂着一面夏威夷州旗。在接电话之前,埃里克说,盒子里放着一台50英寸的电视,这是最新的捐赠之一。一个朋友送给他一个冲浪板:“你需要减压,兄弟,”他的朋友告诉他。埃里克是一名职业冲浪运动员,他在大火中失去了23块冲浪板。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雷和埃里克的公寓,但埃里克没有看到未来。租金太高了,他说。“对我来说,这里离拉海纳太远了。”
瓦尔递给华丽凯一个破碎的储蓄罐,里面装满了煤烟和烧焦的硬币——这是卡斯科家最后的象征。
“我们明天的计划是什么?”埃里克问站在门口的妈妈。
瓦尔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耸耸肩。这很难知道。
几天后,卡斯科一家又聚在一起。周日下午,他们在海滨公园参加了一场为幸存者举办的免费音乐会。微风凉爽,海水波光粼粼,树木摇曳。来自夏威夷的乐队Common Kings吸引着疲惫的人群,把他们从草坪上的椅子上哄了起来。
雷慢慢地绽开笑容,随着歌声的响起,笑容变得更灿烂了。她开始跟着唱,最后蛇形地走上舞池。埃里克在公园里嗡嗡地转着,向他认识的人打招呼——似乎每个人都认识。他们的孩子爬上树,和朋友们在人群中迷路了。卡利和瓦尔放松地坐在椅子上,拿空气中弥漫的“草药”开玩笑。
据瓦尔说,乐队在最后一首歌中演唱了《O Kou Aloha》,这首歌是多年前为拉海纳鲁纳高中写的。
当歌曲接近尾声时,卡斯科兄弟回到了彼此身边。人群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牵着手,然后举起手来。眼泪从雷和瓦尔的脸上流下来。
然后他们很快就散去了:雷不得不想办法在失去透析中心的工作之前,她还能请多少病假。埃里克去帮助同样流离失所的朋友。瓦尔和卡利离开去看了一套公寓,那是瑞安代表他们申请的——他一共申请了六套公寓之一。
火灾发生三周后,瓦尔和卡利收到了好消息:他们被批准租下瑞安在纳比利找到的一套三居室。瓦尔说她终于可以放松她紧张的肩膀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想起了为拉海纳院子增光的芒果树、橘子树和棕榈树。那里有凯西多年前种下的两棵椰子树,还有她在花园里养的红姜、茉莉花和粉红色和黄色的鸡毛花。那里有一棵栀子花,她花了很多年和它说话,恳求它开花。它终于在今年的母亲节开花了。
大火吞噬了一切。